жҲҝеҺҝж–°й—»зҪ‘и®Ҝ жқҖйқ’жңәзҡ„жё©еәҰзј“зј“ж”ҖеҚҮпјҢе§ҡеҙҺжҠ“иө·дёҖжҠҠж‘ҠжҷҫеҘҪзҡ„йІңеҸ¶йҖҒиҝӣж»ҡзӯ’гҖӮд»ҺиҝҷдёҖеҲ»иө·пјҢиҝҷдәӣйІңеҸ¶дҫҝиёҸдёҠдәҶи„ұиғҺжҚўйӘЁзҡ„еҫҒзЁӢгҖӮ260ж‘„ж°ҸеәҰзҡ„ж»ҡзӯ’еҶ…пјҢйІңеҸ¶иў«иһәж—ӢжқҝеёҰеҠЁпјҢеңЁзӣҙеҫ„80еҺҳзұізҡ„зӯ’еҶ…зҝ»ж»ҡгҖҒжҠӣжү¬гҖӮеңЁзӮҪзғӯзҡ„з©әж°”е’ҢеҗҢж ·зӮҪзғӯзҡ„ж»ҡзӯ’й—ҙжҺҘи§ҰгҖҒеҲҶзҰ»пјҢеҶҚжҺҘи§ҰгҖҒеҶҚеҲҶзҰ»пјҢйІңеҸ¶дёҖиҫ№еүҚиЎҢпјҢдёҖиҫ№жҠҠдҪ“еҶ…зҡ„ж°ҙеҲҶйҖјеҮәгҖӮ

иҢ¶еҶңжӯЈеңЁй«ҳж ҮеҮҶз”ҹжҖҒиҢ¶еӣӯдёӯйҮҮж‘ҳйІңеҸ¶гҖӮ
еҮәеҸЈеӨ„пјҢжқҖйқ’еҗҺзҡ„иҢ¶еҸ¶и·іи·ғзқҖгҖҒе‘јеҸ«зқҖгҖӮиҪҰй—ҙеҶ…пјҢиҢ¶йҰҷејҖе§ӢејҘжј«пјҢжІҒдәәеҝғи„ҫгҖӮ
4жңҲ25ж—ҘпјҢжҲҝеҺҝзӘ‘ж·®й•Үж·®ж°ҙжқ‘дәҢз»„пјҢ45еІҒзҡ„е§ҡеҙҺжӯЈзӣ®дёҚиҪ¬зқӣең°зӣҜзқҖжқҖйқ’жңәпјҢдёҖдјҡе„ҝз”ЁжүӢжҠ“иө·жқҖйқ’еҗҺзҡ„иҢ¶еҸ¶пјҢз”ЁжүӢжҢҮж„ҹеҸ—иҢ¶йқ’зҡ„еҸҳеҢ–пјҢдёҖдјҡе„ҝдҪҺеӨҙжҹҘзңӢзӮүзҒ¶еҶ…зҡ„зҒ«еҖҷгҖӮвҖңиҝҷд№ҲеӨҡе№ҙдәҶпјҢжҲ‘иҝҳжҳҜи§үеҫ—жҳҺзҒ«зӮ’иҢ¶жӣҙжңүж„ҹи§үгҖӮвҖқд»–зҡ„иҜқиҜӯдёӯпјҢж»ЎжҳҜеҜ№дј з»ҹеҲ¶иҢ¶е·Ҙиүәзҡ„жү§зқҖдёҺзғӯзҲұгҖӮ

йҮҮиҢ¶е·ҘеҲқзӯӣиҢ¶йІңеҸ¶гҖӮ
жҲҝеҺҝиҮӘеҸӨдҫҝжңүвҖңеҚғйҮҢжҲҝйҷөпјҢиҜ—й…’иҢ¶йҰҷвҖқзҡ„зҫҺиӘүгҖӮжҚ®гҖҠжҲҝеҺҝеҝ—гҖӢи®°иҪҪпјҢе”җд»ЈжӯӨең°е·ІеҪўжҲҗвҖңдә‘йӣҫиҢ¶вҖқиҙЎе“ҒдҪ“зі»пјҢжҳҺжё…ж—¶жңҹжӣҙеӣ жҜ—йӮ»иҢ¶й©¬еҸӨйҒ“пјҢжҲҗдёәй„ӮиҘҝеҢ—ең°еҢәиҢ¶еҸ¶йӣҶж•ЈйҮҚй•ҮгҖӮж·ұеҺҡзҡ„иҢ¶ж–ҮеҢ–еә•и•ҙпјҢеҰӮеҗҢдёҖе№…еҸӨиҖҒиҖҢз»ҡдёҪзҡ„з”»еҚ·пјҢеңЁиҝҷзүҮеңҹең°дёҠеҫҗеҫҗй“әеұ•ејҖжқҘгҖӮ
2014е№ҙпјҢеңЁеӨ–й—ҜиҚЎеӨҡе№ҙеҗҺпјҢе§ҡеҙҺеӣһеҲ°е®¶д№ЎпјҢдёҖеӨҙжүҺиҝӣгҖҠиҜ—з»ҸгҖӢдёӯжүҖиҝ°зҡ„вҖңеұұжңүеҳүеҚүвҖқзҡ„еҺҹе§ӢиҢ¶жһ—пјҢжҠҠиҮӘе·ұеңЁеӯҰж ЎйҮҢжүҖеӯҰзҡ„дё“дёҡзҹҘиҜҶжҢҘжҙ’еңЁиҝҷзүҮж–Үи„үиҠійҰҷзҡ„иҢ¶еӣӯйҮҢгҖӮ
вҖңиҷҪ然жңәеҷЁиғҪжҸҗй«ҳж•ҲзҺҮпјҢдҪҶжғіиҰҒи®©иҢ¶йӯӮиӢҸйҶ’пјҢиҝҳеҫ—йқ жүӢе·ҘгҖӮвҖқе§ҡеҙҺдјёеҮәеҸҢжүӢпјҢйӮЈеёғж»ЎиҖҒиҢ§зҡ„жүӢжҺҢдёҠпјҢжҳҜиў«иҢ¶жұҒжөёж¶ҰеҗҺйҡҫд»Ҙжҙ—жҺүзҡ„иҢ¶иүІпјҢжҳҜеІҒжңҲдёҺиҢ¶йҰҷз•ҷдёӢзҡ„зӢ¬зү№еҚ°и®°гҖӮ
вҖңжё©еәҰе·®дёҚеӨҡдәҶгҖӮвҖқд»–зҡ„жүӢжҺҢжӮ¬з©әеңЁйҫҷдә•й”…дёҠж„ҹзҹҘжё©еәҰпјҢеҠЁдҪңзІҫеҮҶпјҢеҰӮеҗҢеҢ дәәеңЁжөӢйҮҸзҺүеҷЁгҖӮи®°иҖ…жӢҝиө·жё©еәҰи®ЎжөӢжё©пјҢжҢҮй’ҲеҲҡеҘҪжҢҮеңЁ260ж‘„ж°ҸеәҰзҡ„еҲ»еәҰгҖӮ
дёҖжҠҠиӮҘзЎ•зҡ„иҢ¶иҠҪе…Ҙй”…пјҢеҸ‘еҮәиҪ»еҫ®зҡ„жІҷжІҷеЈ°пјҢе§ҡеҙҺеҸҢжүӢжҺўе…Ҙж»ҡзғ«зҡ„й”…еҶ…пјҢйқ’еҸ¶еңЁжҺҢеҝғзҝ»йЈһеҰӮиқ¶пјҢж—¶иҖҢвҖңиҖҒй№°жҠұжңҲвҖқ收жӢўжҲҗеӣўпјҢж—¶иҖҢвҖңзҷҪй№Өдә®зҝ…вҖқжҠӣж’’жҲҗзҖ‘гҖӮвҖңеҝ…йЎ»еҝ«йҖҹең°зҝ»зӮ’пјҢ0.1з§’зҡ„иҝҹз–‘йғҪдјҡи®©иҢ¶еӨҡй…ҡиҝҮеәҰж°§еҢ–гҖӮвҖқ

йІңеҸ¶з»Ҹж‘Ҡйқ’еҗҺпјҢиў«жҠ•е…Ҙ260ж‘„ж°ҸеәҰзҡ„й“Ғй”…иҝӣиЎҢжқҖйқ’еӨ„зҗҶгҖӮ
дёҖзүҮе°Ҹе°Ҹзҡ„иҢ¶еҸ¶пјҢжө“зј©зқҖж—ҘжңҲеӨ©ең°зҡ„зІҫеҚҺдёҺзҒөжҖ§гҖӮе”ҜжңүдҝқжҢҒе…¶еӨ©з„¶жң¬жҖ§пјҢжүҚиғҪжҲҗе°ұжңүжңәзҡ„й«ҳз«ҜеҘҪиҢ¶гҖӮ
е§ҡеҙҺзҡ„зңјзҘһзҙ§зҙ§зӣҜзқҖй”…дёӯзҡ„иҢ¶еҸ¶пјҢдёҚж”ҫиҝҮд»»дҪ•дёҖдёӘз»Ҷеҫ®зҡ„еҸҳеҢ–гҖӮеҪ“иҢ¶еҸ¶еңЁй”…дёӯйҖҗжёҗеҸҳеҫ—жҹ”иҪҜпјҢд»–дҫҝи°ғж•ҙжүӢжі•пјҢз”ЁжүӢжҺҢиҪ»иҪ»жҢүеҺӢгҖҒжҸүжҗ“пјҢи®©иҢ¶еҸ¶еңЁй«ҳжё©дёҺеҺӢеҠӣзҡ„еҸҢйҮҚдҪңз”ЁдёӢпјҢйҖҗжёҗиӨӘеҺ»йқ’涩пјҢйҮҠж”ҫеҮәж·Ўж·Ўзҡ„жё…йҰҷгҖӮеңЁиҝҷдёҖ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»–зҡ„еҸҢжүӢе§Ӣз»ҲдёҺй“Ғй”…дҝқжҢҒзқҖжҒ°еҲ°еҘҪеӨ„зҡ„и·қзҰ»пјҢж—ўдёҚи®©иҢ¶еҸ¶еӣ еҸ—зғӯдёҚеқҮиҖҢз„ҰзіҠпјҢеҸҲиғҪе……еҲҶжҝҖеҸ‘иҢ¶еҸ¶зҡ„йҰҷж°”гҖ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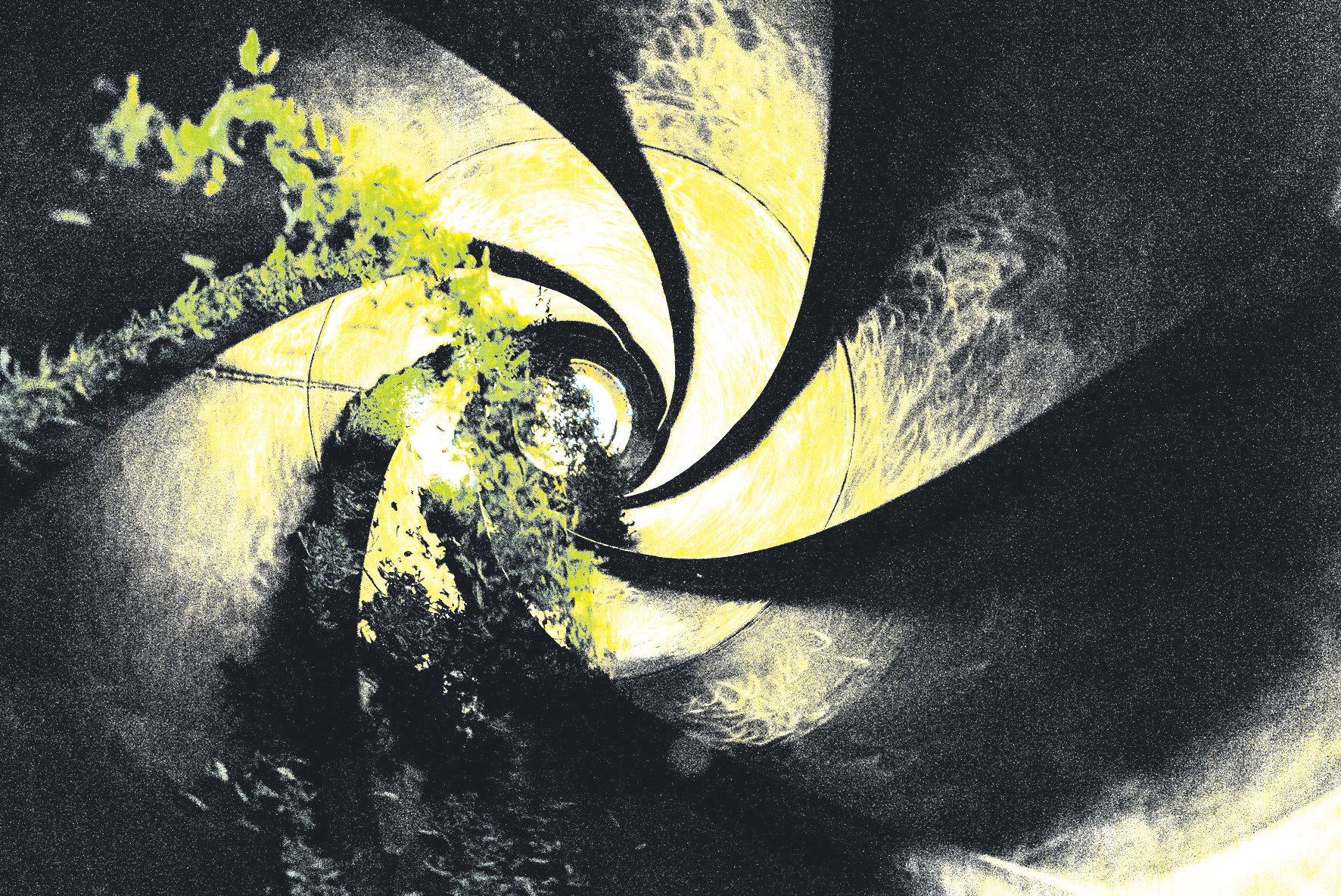
йІңеҸ¶еңЁе®ҡеҲ¶зҡ„дё“з”Ёи®ҫеӨҮдёӯжқҖйқ’гҖӮ
йҡҸзқҖзҝ»зӮ’зҡ„жҢҒз»ӯпјҢй”…дёӯиҢ¶еҸ¶зҡ„йўңиүІжёҗжёҗеҸҳж·ұпјҢд»ҺйІңе«©зҡ„зҝ з»ҝиҪ¬дёәжІүзЁізҡ„еўЁз»ҝпјҢз©әж°”дёӯзҡ„иҢ¶йҰҷд№ҹж„ҲеҸ‘жө“йғҒгҖӮе§ҡеҙҺзҡ„йўқеӨҙеёғж»Ўжұ—зҸ пјҢйЎәзқҖи„ёйўҠж»‘иҗҪгҖӮдҪҶд»–жө‘然дёҚи§үпјҢе…Ёиә«еҝғең°жҠ•е…ҘеҲ°дёҺиҢ¶еҸ¶зҡ„вҖңеҜ№иҜқвҖқдёӯгҖӮд»–зҹҘйҒ“пјҢжӯӨеҲ»жӯЈжҳҜеҶіе®ҡиҢ¶еҸ¶е“ҒиҙЁзҡ„е…ій”®ж—¶еҲ»пјҢзЁҚжңүз–ҸеҝҪпјҢд№ӢеүҚзҡ„еҠӘеҠӣдҫҝеҸҜиғҪд»ҳиҜёдёңжөҒ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д»–зҡ„еҠЁдҪңжӣҙеҠ и°Ёж…ҺпјҢеҠӣеәҰд№ҹжӣҙеҠ еқҮеҢҖпјҢжҜҸдёҖж¬Ўзҝ»зӮ’гҖҒжҜҸдёҖж¬ЎжҢүеҺӢпјҢйғҪеғҸжҳҜеңЁйӣ•зҗўдёҖ件зІҫзҫҺзҡ„иүәжңҜе“ҒгҖӮ

жқҖйқ’еҗҺзҡ„иҢ¶еҸ¶еҶҚз»ҸеҶ·еҚҙпјҢ然еҗҺиў«ж”ҫе…Ҙз«№зӯҗеӣһжҪ®пјҢдёәдёӢдёҖжӯҘзҡ„жҸүжҚ»еҒҡеҮҶеӨҮгҖӮ
иҢ¶еҸ¶иў«з”©еҮәгҖҒжҠ–ж•ЈгҖҒ收жӢўвҖҰвҖҰиҢ¶йҰҷи…ҫз©әиҖҢиө·пјҢиҢ¶еҪўејҜдјјйұјй’©гҖҒзҷҪжҜ«жҜ•зҺ°гҖӮвҖңеҮәй”…пјҒвҖқе§ҡеҙҺжҠ№дәҶжҠҠжұ—пјҢзҒ«е…үжҳ еҫ—д»–зһід»ҒеҸ‘дә®пјҢйўқеӨҙзҡ„жІҹеЈ‘жҳҜеҚҒдҪҷе№ҙжқҘдј жүҝйқһйҒ—жҠҖиүәзғҷдёӢзҡ„вҖңе№ҙиҪ®вҖқгҖӮ
вҖңиҢ¶дәәзҡ„жүӢиҰҒеғҸиҝҷзүҮеҸ¶еӯҗдёҖж ·вҖ”вҖ”з»Ҹеҫ—иө·жҸүжҚ»пјҢе®Ҳеҫ—дҪҸжң¬еҝғгҖӮвҖқе§ҡеҙҺеҲ¶иҢ¶пјҢе§Ӣз»Ҳз§үжҢҒзқҖвҖңеҒҡиүҜеҝғиҢ¶вҖқзҡ„дҝЎеҝөгҖӮд»ҺиҢ¶еҸ¶зҡ„йҮҮж‘ҳеҲ°еҲ¶дҪңе®ҢжҲҗпјҢжҜҸдёҖдёӘзҺҜиҠӮд»–йғҪдёҘж јжҠҠжҺ§пјҢеҠӣжұӮе°ҶиҢ¶еҸ¶зҡ„е“ҒиҙЁеҸ‘жҢҘеҲ°жһҒиҮҙгҖӮеңЁжҸүжҚ»зҺҜиҠӮпјҢд»–ж №жҚ®иҢ¶еҸ¶зҡ„дёҚеҗҢзү№жҖ§пјҢиҝҗз”ЁжҒ°еҲ°еҘҪеӨ„зҡ„еҠӣеәҰпјҢдҪҝиҢ¶еҸ¶зҡ„з»Ҷиғһз»„з»Үз ҙиЈӮпјҢдёәеҗҺз»ӯзҡ„еҸ‘й…өе’ҢйҰҷж°”еҪўжҲҗеҘ е®ҡеҹәзЎҖгҖӮеңЁе№ІзҮҘ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»–жӣҙжҳҜе…ЁзҘһиҙҜжіЁпјҢе……еҲҶи°ғеҠЁе—…и§үгҖҒи§Ұи§үгҖҒи§Ҷи§үпјҢз”ЁзІҫйӣ•з»Ҷзҗўзҡ„еҢ дәәзІҫзҘһпјҢз…ҺеҮәдёҖжқҜжқҜжё…йҰҷжҖЎдәәзҡ„еҘҪиҢ¶гҖӮ

иҢ¶еҸ¶еңЁйҫҷдә•й”…дёӯз»ҸжүӢе·ҘзҗҶжқЎгҖҒзғҳе№ІпјҢйҖҗжёҗз”ұз»ҝиүІиҪ¬дёәз“ҰзҒ°иүІгҖӮ
вҖңеҒҡиҢ¶еҰӮеҒҡдәәпјҢж—ўиҰҒе®ҲдҪҸж №жң¬пјҢд№ҹиҰҒж•һејҖиғёжҖҖгҖӮвҖқжҡ®иүІдёӯпјҢе§ҡеҙҺдҪҚдәҺжҲҝеҺҝиҘҝе…іеҚ°иұЎжҷҜеҢәзҡ„зӣҙж’ӯй—ҙеҲ«жңүдёҖз•Әйҹөе‘ігҖӮд»–жІЎжңүйҖүжӢ©еёёи§Ғзҡ„еҸ«еҚ–ејҸзӣҙж’ӯпјҢиҖҢжҳҜд»ҘжҲҝйҷөе®«е»·ж–ҮеҢ–гҖҒйҘ®йЈҹж–ҮеҢ–дёәиғҢжҷҜеЁ“еЁ“йҒ“жқҘгҖӮжүӢжҢҒзқҖж–°еҲ¶зҡ„вҖңжҲҝйҷөиҢ—е“ҒвҖқпјҢе°ҶиҢ¶жұӨеҖҫе…ҘзҺ»з’ғжқҜдёӯпјҢз»ҝиүІзҡ„иҢ¶жұӨеңЁжңҲе…үдёӢжөҒиҪ¬зқҖеҚғе№ҙе…үеҪұгҖӮиҢ¶йҰҷеӣӣжәўй—ҙпјҢвҖңе…іе…ійӣҺйё пјҢеңЁжІід№ӢжҙІвҖқзҡ„зҲұжғ…ж•…дәӢпјҢжңүдәҶе…Ёж–°зҡ„жј”з»ҺгҖӮ
д»Һеұұй—ҙдёҖзүҮеҸ¶еҲ°дёҮ家жқҜдёӯиҢ¶пјҢиҢ¶еҸ¶зҡ„з”ҹй•ҝдёҺж—…иЎҢпјҢи®Іиҝ°зқҖе…ідәҺж–ҮжҳҺдёҺз”ҹжҙ»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ҢжІүж·ҖзқҖдёӯеҚҺж–ҮжҳҺзӢ¬зү№зҡ„д»·еҖјзҗҶеҝөгҖӮйҮҮи®ҝз»“жқҹж—¶пјҢзҷ»дёҠе§ҡеҙҺ家иҢ¶еұұзҡ„жңҖй«ҳеӨ„пјҢдә‘йӣҫж•ЈеҺ»зҡ„еҲ№йӮЈпјҢе°№еҗүз”«йҮҮиҜ—иө°иҝҮзҡ„йқ’зҹіе°Ҹеҫ„дёҺ笔зӣҙе®Ҫйҳ”зҡ„и°·з«№й«ҳйҖҹе…¬и·Ҝзӣёжҳ жҲҗи¶ЈгҖӮиҢ¶жһ—ж·ұеӨ„пјҢж–°иҠҪеңЁеҸӨиҢ¶ж ‘жўўиҪ»иҪ»йўӨеҠЁпјҢдёҖдҪҚжүӢиүәдәәжӯЈз”Ё260ж‘„ж°ҸеәҰзҡ„иөӨиҜҡпјҢиҝҳеҺҹдёҖзүҮеҸ¶еӯҗзҡ„жң¬иҙЁеұһжҖ§пјҢз»ӯеҶҷзқҖдј жүҝдёҺеҲӣж–°зҡ„иҢ¶йҹөзҜҮз« гҖӮ
дёҖе®Ўпјҡе®ӢеЁҘ
дәҢе®ЎпјҡзЁӢиүі
дёүе®ЎпјҡйҫҡжҲҗйҫҷ







